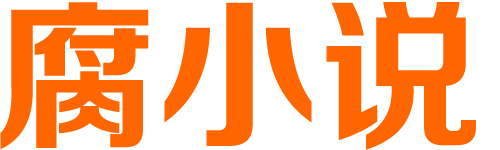以撒怎么了?(74)
比如这天,正是吃晚饭的时间,泽维尔喊以撒却没人应,进房间一看,以撒手里勾着酒瓶,脸颊红扑扑的,歪在床头上打着呼噜。
泽维尔蹑手蹑脚走过去,坐在床边,听见呼噜声掩盖下、胸腔里颤抖的轰鸣。他给以撒捋开挡在脸上的头发,从中间挑出了两根白发,泽维尔低着头沉默片刻,谁也看不见他的表情。
一滴水落在以撒眼角,又顺着脸颊滑落下去,好像哭了似的。到底是谁在哭?
泽维尔深呼吸了一下,用手背擦擦眼睛,打了一盆水来,解开以撒的衣服扣子,他捏着毛巾的手顿了一下,才犹豫地覆上去。
**
在天堂上,看着实时直播的天使们围坐在屏幕前。
“这小子是看上他养父了?”天使甲一边嗑瓜子一边说。
“也难怪。他们地球人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这个。”天使乙说着,在胸口比了一个大波的形状。
不知怎么,原本非常忧郁的、正在拧毛巾的泽维尔,突然打了个大喷嚏。
第65章 远行
那是初秋的一个晚上,不远处教堂整点的钟声回荡在夜色之中。收工回家的以撒披上旧大衣,脑后骤然响起一阵扑棱棱的振翅声,几只海鸟在海面上低低盘旋。快下雨了。他的骨头像泡进了水里,细密的疼痛像针钻进关节。
以撒到家的时候,屋子里是暗的。泽维尔没有在家,只留了张说明要外出的字条,不知道去了哪儿。他开了瓶酒,仰头灌了一口,坐下来休息许久才起身脱了大衣,开始着手给自己弄点东西吃。
虽然以撒总威胁说要饿死泽维尔,但从没这么做过。所以他今天还是准备了泽维尔的那份晚餐——尽管到放凉了也没人享用。
晚上八点,他把晚饭又热了一遍,开始有点担心了。但是想到泽维尔看起来穷得要死,并没有什么可惦记的,于是把一颗心重新咽回肚子里。
以撒倒回床上,又喝了一口酒。
**
快到午夜时,门外终于传来了开门的动静。
泽维尔一矮身踏进门来,脱下大衣,目光落在还热腾腾冒着热气的菜上,踌躇了一会儿才走进卧室。他看见瘫在床头的以撒以及脚边两只空酒瓶子,眉头一皱。
“看看,这是哪个大忙人回家啦?”以撒阴阳怪气地说。他晃晃酒瓶,突然伸长脖子凑过来,像要叨泽维尔一口似的,深深吸了一口气,“噢,你去见女人了?”
“没有,”泽维尔说,“是宴会。”
“那些老爷夫人们不嫌你穷?……你的衣服是哪儿来的?”
“上次跟你说的那位公爵给的,”泽维尔伸手要拿走以撒手里的酒瓶,“别喝了。”
“干什么,”以撒抬手一躲,用已经带着点醉意的眼睛睨他,“轮得到你管我?”
泽维尔沉默了一会儿,换了个话题:“怎么等到现在?”
“等你吃饭,混蛋。”
“……我已经吃过了。”
“那你怎么不和我说一声?”
“我怕我写了你看不懂。”
“他妈的就你有文化!”以撒毫无预兆地发了火,站起来像要用酒瓶子打泽维尔,突然又“哎哟”一声倒回床上。
泽维尔吓了一跳,正要去扶他,被以撒一巴掌拍开了手。
“你怎么了,腰痛?”泽维尔说,“我给你揉揉吧,以撒。”
“……不需要!我睡觉了。”
说着,以撒喝光了酒,把空瓶子往泽维尔怀里一塞,拉起被子盖到头顶。
泽维尔费老大劲儿才把以撒从被子里刨出来,一字一顿地说:“以撒,你要去看病。”
“用不着!说的好像家里钱很多似的。”
“你别担心钱的问题。”泽维尔说着,从内袋里摸出一只钱包,塞进以撒手里,沉甸甸的份量把以撒吓了一跳。
他一骨碌爬起来,把钱从袋子里翻出来数了一通,颤巍巍地问:“你偷了谁啊?”
泽维尔噗地笑开了:“正经钱。公爵给我的。”
“放屁!谁会无缘无故给你送这么多钱?”
“不是无缘无故。我要去伦敦了。”
以撒瞪大了眼睛,顿时就清醒了。
“……你去做什么?”
“做他的秘书。”
“可是,伦敦!……那么远!”以撒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一年回来一趟吧。”
以撒愣了一下,又问:“你平常大门不迈二门不出,怎么突然想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泽维尔叹了口气:“你不是总盼我出去做事吗?”
“这……”以撒问,“你什么时候走?”
“月底。今年的圣诞节,很可能也不回来。”
**
泽维尔已经很长时间不跟以撒一起睡了,15岁那年,以撒帮他在旁边牵了一张吊床。但今晚,他半夜摸索着躺在以撒身边,两个人挤成一团,以撒也没有说什么。
“你会想我吗?”泽维尔问。
“想又怎么样?你总归是要走的。”
“我有机会就回来看你,每个月寄钱来。等我有了稳定的收入和住处,就把你接到伦敦去。”
“傻小子,说不定哪天大富大贵就忘了我呢!别给我这样的盼头。你自己的日子自己过吧,我嘛,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怎么会是那种人?”泽维尔争辩说。然而,回应他的只有浅浅的鼾声。
以撒的呼吸间都是酒味,嘴唇也湿漉漉的,不知道为什么,泽维尔看他这毫无防备的样子就突然感觉很不高兴,用手背狠狠地给他擦擦嘴——以撒被这粗暴的动作闹醒了,睁开迷蒙的眼睛,笑眯眯地捞起泽维尔的手,暧昧地摸摸他的手背,或许是把泽维尔当成了哪个女人,突然叭地亲了口带响的,这可把泽维尔吓了一大跳。
以撒含含糊糊地嘟囔着别人的名字,眼睛一闭,又睡着了。
泽维尔愣了一下,几乎想蹬他一脚才好。但最后他也卷了枕头被子回到吊床上去,整晚辗转反侧,吊床随着他的动作吱呀作响。
在泽维尔睡熟之后,以撒撩起眼皮,定定地看着吊床上的背影,叹了口气。
**
临走前,以撒帮泽维尔把行李搬上船,又赶回去做自己的事。
泽维尔站在甲板上,远远看见以撒在烈日下扛着木箱子,汗水把浅色的裤腰染湿一片;那头乱糟糟的红发短短地束在脑后,露出后颈。哪怕只有这样一个背影,而且隔着这么远的距离,泽维尔也仿佛能听见他湿热而沉重的呼吸。
船笛轰鸣时,以撒下意识循声望去,看见甲板上凭栏的泽维尔。他脚步一顿,抬手刚想打招呼,突然看见了泽维尔身后衣着讲究的老人——想必就是那什么公爵吧,于是,以撒的手悬在半空,假装抬起手擦汗,然后默默转身,越走越远。
“你认识那个船工?”老人问泽维尔,“他好像想和你打招呼。”
泽维尔沉默了一会儿说:“太远了,看不清。也许是常去教堂做礼拜的信徒吧。”
“噢,对,我记得……你是不是做过牧师?穷人想必很难应付。不过没关系,以后你就不必再迎合他们了。”
泽维尔笑着点点头,搭在栏杆上的手交握在一起,指关节捏得发白。
他后来总是想起这天,想起以撒高高卷起的衣袖、健壮的胳膊,还有码头工人特有的麦色皮肤,不知道为什么竟不敢承认这是他的养父。也许知识真把他变成了一个有点傲慢又自卑的家伙,但否定自己的出身就能保全敏感的自尊心吗?
作为一个利物浦来的底层小乡巴佬,伦敦注定会使他黯然神伤。尽管公爵越来越信任泽维尔——从一开始只请他帮忙给书信润色到全权由他代笔,泽维尔的地位还是没有根本的改变,他平常穿的也是仆人的衣服,和仆人住在一块儿,甚至还会遭到这些城里来的家仆的排挤。
喜欢本文可以上原创网支持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