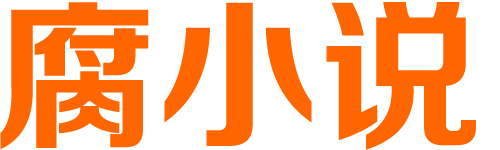以撒怎么了?(14)
以撒身上的那个人肩膀抖动了一阵,可能在笑。这个要求显然是荒谬的。
泽维尔重重拍了一下门,向后退了两步,没在门前继续浪费时间,立刻转身跑去向其他狱警求助,脚步声匆匆远去。
“你的漂亮医生是个废物。看,他搬救兵去了,留你一个人在这里,”余低下头,凑在以撒耳边,神经质地低笑着,“既然醒了就睁开眼睛吧。告诉我你究竟是什么,以撒?”
以撒沉默了片刻,长长叹了口气:“看到不该看的东西让你害怕了?”
这时,门外重新响起了呼喊和撞门的声音,门框附近脆弱的墙皮簌簌落下。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余警觉地起身,突然后颈被扣住并向下猛地拉扯,他一头撞上以撒胸口,立刻又被摁住脑袋,一拳打在左颧骨,余立刻无力地滑倒下来,手指还抽搐着。
“既然这么担心死了会去哪儿,活着的时候为什么不珍惜呢。”以撒把余推到旁边,从床上爬起来,没想到本该陷入昏迷的家伙突然扣住他的手腕,另一只手从腰后摸出匕首抬手刺下!在狭小的床位间,以撒躲避不及,白刃擦着骨头刺穿了右臂,他哀嚎一声,余紧接着抽出匕首,然而以撒早有防备,抬脚踹上他小腹,余栽倒在地,匕首不慎脱手,他挣扎着想爬起来,却因为摔着了后脑,眼前一阵一阵地模糊。
以撒紧紧扼着右臂,那道贯穿伤溢出的血打湿了半条袖子,两人粗喘着僵持十数秒,视线同时锁在甩落到不远处的匕首上。
嘭!嘭!门外纷杂的撞击声越来越响。
以撒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抬肘把勉力从地上爬起来的余重新揍趴在地上。这时,泽维尔率先破门而入:“以撒!”
以撒用牙从囚服上撕下一条布料紧紧扎住受伤小臂,坐在床沿,不置可否地歪了歪头。紧张的天使三步并两步走过来,把他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还想翻起以撒的眼皮看看,被摇头晃脑地躲开了。
确认以撒身上的外伤除了手臂处的贯穿之外都不严重,泽维尔的肩膀忽然塌了下来,长吁一口气。他转身简单检查了余的情况,朝门口点点头,马上就有狱警冲上来把他架走;泽维尔又说:“等等。”然后从对面床下又揪出一个惊恐的囚犯来,于是这个人被一起带走了。
沉默地做完这一切,泽维尔在地上蹲了好一会儿才扶着膝盖起来,以撒抬头看他:“你生气了?”
泽维尔身体没动,只有那双蓝眼睛转过来,他冷冷地用余光打量了以撒一会儿,突然说:“你提醒我了。”然后抬手就在以撒的脑袋上扇了一巴掌,把恶魔给打得愣住了。泽维尔根本没打算给以撒反应的时间,拽起他没伤的那条胳膊把他拖拽起来,往医务室走去。
以撒被拽得踉踉跄跄,一边摸着被扇的地方一边想:倒不怎么疼。但是泽维尔怎么了?
**
以撒坐在椅子上,任由泽维尔给他包扎伤口,识趣地自动噤声。突然,他注意到什么,伸手撩开泽维尔的金发,露出耳下圆形的印记——直径大约一指半,呈红色,中间有个形似无限大符号的纹路,也像铁链的其中一环。以撒粗糙带茧的指腹在上面摩挲,自己耳下那片皮肤同时感到轻微的麻痒。他皱着眉松开了手。
“双向的链接,你也有一个,”没等以撒询问,泽维尔就自顾自地解释说,“我自己现在没有一点魔法,只有这样才能监测到你。”
以撒摸摸下巴:“那你牺牲挺大的。”
“你要是真能有这个认识就太好了,”泽维尔一圈一圈地给以撒受伤的小臂绕上纱布,“不过,现在来说说你吧。一个恶魔被人类制住,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吗?”
以撒喉咙里咕噜一阵,没有接话。
“没关系,那我们来确认另一件事:我撞门的时候,甚至在这之前,你醒着。”
以撒的趾爪在地上磨蹭,发出嚓嚓响。
泽维尔深呼吸了一下,尽量用平稳的语气继续发问:“我坏了你的好事吗?”
以撒无奈地耸耸肩:“要是你想听实话的话,对。你不该来。”
“为什么?”泽维尔问。这话是脱口而出的,他没有预想过得到什么样的回答,但是无论如何不应该是这样——
“因为我喜欢,”以撒说,“因为我需要。不是他也会是别人。”
泽维尔听后挑了挑眉,闷闷地笑起来,喃喃着“好,不错”之类无意义的词语,很久才开口:
“听着,我完全知道你放荡、愚蠢,又容易惹是生非;我被你害得倒了大霉,现在还不得不和你捆绑在一起,这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不幸。但是该死的,为什么我就是改不了爱管闲事的毛病?为什么我分明有一万个理由来讨厌你,却总是在为你挂心?”
以撒听了这话,完全愣住了。他好一会儿才回过神,用拳头轻轻搡了一下泽维尔的肩膀:“我知道你是出于好心。但是我就是这样的,我喜欢有人操我,哪怕这个人我不喜欢。所以我才是魅魔。”
以撒的直率让土生土长的英国天使瞠目结舌。哪怕身在底层的时候他也没有听过这种完全无视廉耻的发言,但更古怪的是,如果说面前的魅魔并非出于勾引,只是未开化的原始本性,似乎也很可信。或许分食禁果的时候漏了他那份,所以他不必遵循被伊甸园拒之门外的那些人定下的条例。
“有些事情说来比较复杂。自从伦敦又开始下雨了……呃,”以撒说到这里突然面色古怪地摸摸嘴唇,“这不能说吗?好吧。”
泽维尔听到以撒嘴里前言不搭后语的怪话,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真的受限于保密条例——这个条例并不是一纸文件,而是一管纳米单位的小东西,植入保密者的脑袋里,当保密者试图用任何方式透露出需要保密的内容,就会被自动替换成提前设置好的一句毫不相关的话。
“你看,我说了很复杂吧。总之因为各种原因,”以撒指指脑袋,无奈摊手,“我很需要肢体接触。长时间的拥抱、亲吻,或者来干我。做很多次或者一次很多人。”
“这…!好了我知道了。不是,我不知道;不是,等等,但是我想你可以——我希望你最好可以不要这么直白。”泽维尔感到事情很棘手,以至于说出口的每个单词都有点烫嘴。他焦虑地在医务室里踱来踱去,突然,他发现了盲点,锐利的目光直锁住一脸无辜的以撒:“你不能找个比较长久的伴儿吗?”
“人类差不多就活70岁吧,而且伦敦又下雨了——搞啥,这也不能说吗?”以撒说,“没事,原因不重要,我基本讨厌所有人。”
“但是你这样怎么行呢,”泽维尔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总得挑挑人吧,毕竟你……唉。”你实在不像那种发现不对就会中途叫停的人。
以撒坐着不动,绿眼睛随着泽维尔的走动转过来转过去。他觉得泽维尔焦虑地走来走去的样子太好玩儿了。这是他见过最像天使的天使,金发蓝眼,身材高挑,长着一张不算顶漂亮但十足惹人怜爱的脸,很疲惫、很忧愁,絮絮叨叨。
狡猾的魅魔酝酿了一下,摆出一副比天使更忧愁的表情:“唉,你不知道我的苦衷,所有人都讨厌我。路边的狗都有人摸摸,我没有。我现在睡得越来越长了,因为醒着的时候总是很焦躁……”他说一句就抬眼看一下泽维尔,看起来像个失魂落魄的潦倒中年人,还是已经坐在江边大桥栏杆上的那种。
果然,泽维尔的表情一层一层地软化,和当初那个铁石心肠抬手就是一巴掌的冷漠家伙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尚且神志清醒的他也不敢随口问:“怎样能帮到你?”就怕听到他实现不了的要求。
“泽维尔先生,你买下我,不觉得就应该对我负责吗?”以撒看他不为所动,用极度郁闷的语气再加一码,“唉,算了,对不起,当我没说过。在期待什么呢?以撒,你只是一个没人要的老婊子。”
喜欢本文可以上原创网支持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