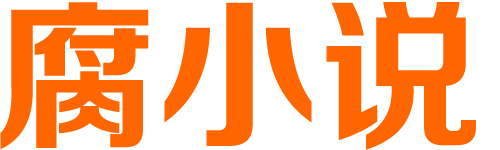以撒怎么了?(48)
泽维尔长长叹了口气。
**
虽然不适的症状消失了,但以撒还是强迫泽维尔卧床休息了大半个钟头。下午,泽维尔决定去找一趟路易:“他不是内科医生吗?正好找他看看病。”
午祷之后,正是工作时间,照理说路易应该在药房待着,但是当两人来到药房,里面只有一个修士在桌前看书。
“路易修士呢?”泽维尔问。
“他半小时前离开了。”修士说。
“他有没有告诉您他去了哪儿、什么时候回来?”
“您身体不适吗?如果症状轻微,我也可以帮您拿点药……”
“不,谢谢,我很好,只是找他有事。”泽维尔连忙说。
“路易修士没有告诉我他去哪儿,不过估计跟加文在一起吧?今天早上加文来取药,我看他们聊了很久。”
“原来如此,”泽维尔说,“路易和加文的关系很好吗?”
“应该是的,”那修士笑起来,“加文性格腼腆,几乎只和那么几个人说话。”
“如果我没记错,加文是——”
“誊写师。他应该在藏书阁待着。”
“谢谢您。对了,丹尼尔修士今天似乎身体抱恙,我出门之前,他托我给他找个医生来。”
“哦,怪不得今天午餐时我没见到他。他能下床吗,还是需要我过去?”
“我想还得麻烦您过去一趟。假如无人应门,也许是他正在昏睡,敲门大声些也无妨。”
**
辞谢了药房里的修士,两人又往藏书阁去。
今日天气晴好,大部分修士都在户外,一排的书桌只坐了两人,走近一看,果然是路易和加文。
泽维尔向他俩打了招呼,然后说:“我在药房没看见您,路易修士。”
“噢,”路易放下笔,“您找我有什么事?”
“今天真是多事之日呀。我也感觉不太好,可能是胃的毛病,但和平常的状况不同,我不敢贸然吃药,想找个医生看看。”
“有这样的意识是对的,假如药不对症,胡乱服用可能更容易出问题,”路易说,“不过我有在药房留一个伙计,您没看见他吗?”
“我碰见他了,在路上。”
“他上哪儿去?”
“说是丹尼尔有些头晕,请他去看看,具体我也不知道。”
“今天的病号真是多得非比寻常,怎么会这样?请稍等,”路易俯身向加文低语了些什么,然后站起来,“身体是容不得耽搁的,请随我来。”
路上,路易问:“您和他谈过了吗?我是指丹尼尔。”
“是的,就在早上。”
“……”
来到药房,里面果然空无一人——毕竟原本那个伙计可是被泽维尔给支走了。路易尴尬地笑笑,请泽维尔坐下,照例看了看眼睛和口腔,然后细细询问他的症状、服药情况,看起来确实是比较专业的医生。
泽维尔问起这件事,路易说:“我定居马赛的时候,在当地一间很有名的诊所做学徒。”
路易看过后认为泽维尔患的可能是溃疡性疾病,目前看来并不严重。然后根据症状给他开了点药。
等着取药的时候,泽维尔闲谈似的问:“您和戴维兄弟俩关系不错?”
刻意提到戴维的时候,泽维尔很仔细观察他的表情,只见路易的神色暗淡了一瞬,沉默半晌才说:“是的,我和他们两兄弟是好友。对了,丹尼尔没有冒犯您吧?请千万别放在心上。听说他有遗传性的疾病,近几年身体状况不佳,尤其在戴维走后,很容易大动肝火。修道院的医疗条件只能简单治疗常见病,我检查不出具体情况,之前劝他去城里的诊所看看,他却总是拖延。”
“他会去的,”泽维尔温声说,“我劝过丹尼尔修士了。”
路易露出惊奇的神色:“真的?看来你们相谈甚欢。”
“他还没有从阴影中走出来,但已经在行动了,相信您看得出来。”
“噢,是的,愿主保佑。”
“说到底还是要感谢您,”泽维尔说,“丹尼尔说最难熬的日子他向你告解时说了不少胡话,如果没有您的聆听,也许我没法这么顺利和他搭上话呢。”
“胡话?哦,是了。唉……遇到那种情况,有时候显得过激也是人之常情。”
“丹尼尔修士没有告诉我他具体说了什么,不过我猜,他是怀疑到某人吧?他似乎不相信戴维会选择自杀。我不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有些猜测对案情的进展可能有实质性的帮助……”
“抱歉,”路易听出弦外之音,及时打断泽维尔,“我不明白,戴维的事和那位侦探的失踪案有关系吗?”
“有的,”泽维尔说,“很可能有。”
“我也想帮助您,泽维尔先生。但很抱歉,告解的内容我无可奉告。哪怕一个杀人犯在告解时向我坦白了一切,我也不能告诉警察一个字,这是我们的原则,我想这您也清楚的。”
泽维尔不勉强他,转而问为什么和加文在一起。
路易解释说:“今天加文身体不适,我来帮他抄写经文。”
“我对加文的情况也略有耳闻,”泽维尔说,“可惜我跟他完全不熟悉,他似乎不是易于交流的那种人。”
“有的人生性腼腆,这也没办法,不过加文其实很善良呢。他之所以不和大家交往,就是担心自己哪天蒙主恩典,留在世上的朋友会感到痛苦。”
“那您就不怕痛苦吗?”泽维尔问。
“人生本就悲辛无尽,不是吗?”路易反问。
他用纸扎好药,交给泽维尔,因为还打算去找加文,就匆匆告辞了。
泽维尔解开纸袋查看里面的药物,以撒靠在门框上看着年轻人匆匆离开的身影,转头说:“喂,兰登。可能路易自己不知道,但我觉得他爱加文比你爱我要多呢。”
“是吗?”泽维尔说。
第40章 无效证件
次日,周日。
这天是个难得的好天气,清早放晴了个把钟头,原以为会一直热下去,接档的却是阴天,云雾如丝,潮湿却不至滴下雨来。
这么好的天气,如果是在肯辛顿,泽维尔一定要出去走走不可。然而今天的他却异常疲惫,慢腾腾地回复完戈登又一次寄来催促他复工的信,端着一杯热茶在窗口坐了一整个上午。
“好像晚年生活啊。”他感叹。
“我真想象不到你老了是什么模样,”以撒说,“英国人,你会秃吗?”
泽维尔对头发和羽毛的问题总是敏感过头,要是平常听到这话,会跳起来也不一定。但是今天,他只是手一抖,故作冷静地吹了吹茶,翻个白眼,一句话也没说。
以撒拧起眉:“你真的病了,泽维尔。”
泽维尔没有回答,只是出神地往外眺望。
今天是礼拜日,修道院里明显比平常热闹一些,也能看见修女们的身影,她们大多在为圣餐忙前忙后。
如果身处工厂或者庄园,现在一定已经吵翻了天,但修道院里的情况却完全不同。虽然规矩不至于严苛到要求在吃饭时打手语交流,不过如果没有非必要的交谈,大家都默认不开口。因此,即便这么多人来来去去,也几乎像默剧一样安静。
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序,如果是保守的院长站在窗口看见这一幕,想必会感到很欣慰吧。
“你好像在等什么?”以撒问。
“等一个人来。”泽维尔说。
话音刚落,就响起敲门声。
**
以撒去开门,院长站在门口,往里张望着,问:“泽维尔先生在吗?”
以撒从门口让开,泽维尔见到院长也没有站起来打招呼,只是微微颔首,生怕别人看不见他苍白的唇色。
“天啊,您这是怎么了?”院长问。
喜欢本文可以上原创网支持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