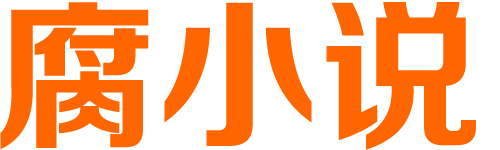沉入地球(64)
程声没开口,手在膝盖上快磨出火星。
听到旁边的人没反应,张立成又说:“你和我儿子是那个对吧?”
这回程声把头低下去,再不开口了。
“你是不是想问我怎么知道的?”
张立成把眼眯起来,整张脸被大太阳晒得通红,面上没一丁点张沉的影子,如果不说没人以为这是张沉爸爸。他就这么惬意地晒太阳,不等程声回答便自顾自接着说:“都知道,张沉的同学、老师、街坊邻居、整个云城都知道他是个喜欢男人的同性恋,你当年那惊天动地的一闹,他在这地方是彻底身败名裂了。那时候连隔壁床病友也偷偷摸摸背着我聊,说张沉和他妈一样,都喜欢勾搭男人。”
张立成还问:“你是不是老天派来故意折腾我家的?你一来我们就要家破人亡,你怎么又来了?”
这次程声终于出声了,但只是几个沙哑的音节,他低着头说:“对不起,对不起,我那时候太喜欢他了。”
张立成摇摇头,转口道:“你觉得我们需要你的对不起?”他继续说:“我儿子好出息,他不在意这些,那么多人讨厌他,他根本无所谓。他从小学到高中每一次都考第一名,比我和他妈强多了,我们连一句英文都不会说,张沉后来做的工作可是拿英文编码呢。你知道吗?从小张沉就被老师说是神经病、自闭症,小时候其他小孩不喜欢他,污蔑他偷钱,说他骂老师,把他作业撕了扔在雪地里,在他校服背后写脏字,张沉他妈妈还在的时候就带着他去学校里跟校领导闹哇,说我们儿子根本不可能做这种事,张沉可是在学校里捡到一块钱都会交给老师、日记本里乖乖写老师今天教了什么的孩子,院子里的爷爷奶奶全都喜欢他。可你那一场闹完,他又被人说同性恋、艾滋病,这下连院子里的爷爷奶奶也避着他走。”
程声咽了口口水,来回摸着自己膝盖,嘴里反复念叨:“对不起,对不起。”
可张立成置若罔闻,他只是太久没和人说这些话,不需要别人回应,只需要源源不断向外排泄。
他还在讲,讲张沉小时候被其他小孩带去山上探险,大雪天里被扔在山上冻了一整晚,李小芸第二天把他从山上找回来,抱着冻僵的孩子哭,还讲他最初住院那几年总能看到张沉的手在流血,张立成问他,得到的答案有时是冻裂了,有时是在餐馆洗盘子时不小心划到手,有时是练琴练得太久。练琴这个答案很让张立成不屑,那时候他就会问:“张沉,你练什么琴?吉他?钢琴?就你还学钢琴?哪有人快二十岁才开始学钢琴?你为了融入上等社会就这么努力?你是不是被你从前那个相好的蛊红了眼?可人家是什么家庭你是什么家庭?你怎么就没点自知之明?”
张立成又想起一码事,仰着头晒太阳,悠闲地说:“可就这样,好多姑娘喜欢张沉呢,因为他搞些破音乐,还遗传了他妈妈的脸,你们这些文化人不知饥饱就搞些神神叨叨的东西,真是脑子有病,有一个甚至追到这里来找我,说自己为了爱情坐了十几小时火车才找来,我看着她想,这么漂亮一个姑娘怎么会喜欢张沉?所以我对她说,姑娘啊,你看我儿子像是能跟人产生爱情的人吗?他现在怕是连人类都不喜欢了。”
旁边程声的胳膊开始打哆嗦,央求着:“别说了,求求你,别说了。”
张立成转头拿那副骨碌碌上下转的眼睛打量程声,又问:“那你和我儿子谁是干的谁是被干的?还是换着来?”他琢磨着,看了程声消瘦的身体许久,像是恍然大悟:“你这么瘦,又不如张沉高,肯定是你被干。”
他又瞧上程声的脸,想到他家里,好像在某些方面扳回一局,点着头感慨道:“张沉搞同性恋能搞到你这样的也不亏,我儿子太好强了,什么都要最好的,哪怕搞男人也要搞最好的男人。”
程声腾地站起来,想往出走,可紧接着外面的门微弱响了一声,张沉拿着缴费单走进来,脚步声很轻,很温柔,程声听着这样的声音怎样也无法把刚刚张立成的话和张沉联系在一起。
屋里瞬间静下来,张立成靠着轮椅的背佝起来,闭上眼抿起嘴,悠然自得晒太阳。
张沉看着对面身体止不住打战的程声,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轻声问:“你怎么了?”
“没事。”
张沉知道有事,却没问什么多余的话,最终只拍拍他的肩,说话语气放缓放柔和,“跟你说别来,你非要来。”
第49章 回家2
墓园在城郊,没人管理,风吹日晒倒了好几座碑。四周种着层层冬青树,这座墓园因为离城中心远才免于被夷为平地的命运,里面也不大讲究,地上盖着一茬茬枯黄短草,里面稀疏立着排排青灰色石碑,远看却是黑压压一片。但仔细看,一块最普通的石碑旁打了排扎眼的木桩,不知道的还以为谁在恶作剧,可再看,那排木桩正好打在墓碑旁,等齐等宽等高,好像要和那碑的主人共存亡,或是要守护她。
晚上去墓园时程声精神一直不好,黑夜里张沉看了他很多次,最后猜张立成跟他灌了些不入耳的难听话,于是把他往自己这边揽过些,眼睛看着黑夜里的碑,话却是对他说:“我爸那人神经病,他跟你说什么都不用在意。”
程声轻轻说了一句“好”,却猛地跪在李小芸墓碑前,连着磕了好几个响头。
原本在另一排碑前烧纸的海燕听到突如其来的动静吓了一大跳,等听清这一阵咚咚咚原来是程声对着碑磕头,倒是松了口气,嘴里嘟囔着:“有钱没钱,有权没权,该难受该愧疚倒是一样不少,没比我们好到哪里去。”
旁边的张沉站得笔直,朝墓碑的方向轻轻叫了声妈,周围寂静得慌人心,这短短一声在黑夜里还生出回音,张沉忽然想起那些赎罪的佛经,他以为没必要,因为已经过去太久,久到他快要忘记这个人的脸,再看到这张新面孔时他已经不想再记起这些事,他全都快要忘记了,小时候说他神经病的老师、冬天把他扔在山上的一群小孩、因为同性恋避着他走的老人,张沉早已不记得这些人长怎样一张脸。于是他又轻轻对着妈妈的墓碑说:“你原谅他吧,这个人比我还倔,你如果不原谅他,他这辈子都要和自己过不去。”
说完他把手搭在程声肩上,另一只手摸了摸他毛茸茸的头发,在空荡荡的墓园里说:“我替她原谅你了。”
他们三个人烧了许多纸钱包袱,张沉程声在这座碑前烧,海燕在紧挨着的另一排碑前烧,嘴里念叨着:“明明,我对你可够好了,这么多年还没忘记给你烧钱,要知道我自己都没什么钱可花。”
她拿手里的拐杖戳墓碑,耳边全是程声刚刚咚咚咚磕头的声音,忽然就笑了,朝着墓碑的方向说:“明明,我总以为你死得早,死得可惜,可你看,活着也没什么好,程老板这么有钱有势有学问一个人,不也和我们一样痛苦地活着熬着吗?你这样想,有没有舒服一点?”
空荡荡的墓园里回荡着她的话,一旁程声扑通一声坐在墓碑旁的枯草地里,手指时不时在身边这座粗粝的石碑表面摩挲着。
张沉把下午买来的东西全烧完,从随身包里拿出一只铁盒,把从疗养院出来后洗好的照片挑挑拣拣放进去。
程声靠着墓碑,双手抱着摸着,脸上一点害怕的神色都没有,他听到叮咣的声音仰头去看张沉,正好看到他手里一沓照片的边角,哑着嗓子问:“你在干什么?”
“给我妈妈看。”张沉动作很缓很轻,总让人以为被他摸到的东西都被他爱着,吉他、钢琴、人、甚至连照片都不外如此。
他把挑好的照片一张一张放进去,跟底下的程声讲起来:“我妈从来没出过云城,连省会都没有去过,这辈子最大的希望就是我能出去,所以我每去一个新地方就拍些照片寄给她,希望她能去世界其他地方走一走。”
程声忽然伸出手,扶着脏兮兮的土地站起来,因为跪得太久腿上漫上酸麻,刚站起来人就往前一踉跄。
喜欢本文可以上原创网支持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