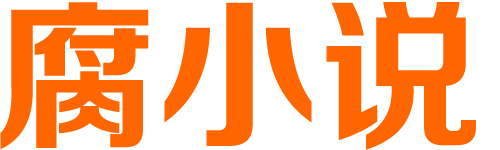沉入地球(109)
他朝女儿扬扬下巴:“闺女,你以后有没有本事给你爸也找个那样家庭的男孩,你爸这辈子就等着享清福了。”
“嘁,我才不呢。”
老板笑了一下,向外看去,路边停靠的那辆黑色轿车已经彻底消失不见,他望着空荡荡的路面,忽然有股怅然若失的感觉,叹了口气,不知是自言自语还是对女儿说:“不过我还真想知道那个小孩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找到他自己口中的爱情。”
云城郊区一片没人管的墓地里,两个男人正并排躺在一座碑前,心有灵犀地望向远处那只和整个新城格格不入的大黑烟囱。
张沉把手伸向空中,透过自己的指缝看那只从小到大陪伴自己的巨大烟囱,忽然发现自己在盯着它看时已经不再会莫名其妙地胃疼。
程声扭过头,望向张沉的侧脸,说:“来的路上有人说这座烟囱要拆。”
“我也听到了,说是要在原地方建一家芯片厂。云城要转型成高新技术城市,烟囱到底还是得拆。”张沉收回望着烟囱的眼神,三两下从地上起来,拍了拍身上沾的草渣,随手从墓碑附近经年累月堆积的钢棍堆里拾起一根钢棍。
程声仰着头,眼睛一直跟随张沉走,他见这人起身动作毫不拖泥带水,又联想到自己整整两个月无法下地走路的经历,咋舌道:“怎么你动作这么利索,好像腿上没钉钢板一样!”他在空中把手伸向张沉的背影,抓着他的背影玩,接着问:“我记得你小时候动不动就胃疼,怎么现在恢复能力那么强?”
“遭多了就能练出来。”
张沉拎着钢棍在妈妈墓前站定,脑海里浮现出十一年前的今天。
那天他把手伸向自己枕头下,从里面摸出一张纸条,那半张纸甚至连遗书都称不上,正面只有寥寥几句话,没有任何抒情与怀恋,全是对儿子未来实打实的交代。
十七岁的张沉看着这张意味死亡的绝笔,并不感到害怕。他刚想把这张纸条塞进口袋,琢磨着找时间烧干净,可不知哪股力量忽然落在他身上,张沉受了指引,鬼使神差把这张纸条翻了过来。
纸条背后有一排铅笔写的小字,模糊不清,被橡皮狠擦过的样子。但主人用的橡皮劣质得厉害,怎么擦也没法把已经写下的字彻底抹去。
张沉凑近这张纸条,一字一字艰难地拼凑着上面难以辨认的小字,他盯了几乎五分钟,一字一字地看,才认出这张纸条背后写了什么。
上面歪歪扭扭的字迹是:不要留下我的任何痕迹,妈妈已经获得了永远的自由。
想到这里,张沉忽然笑了,他举起手里那根沉甸甸的钢棍,挥动着刚痊愈没多久的手臂,用尽全力砸向妈妈的墓碑。
墓园里传来一道巨响,十几年来遭过风吹雨打的石碑早已不堪重负,在挨下第一棍时就屈服地裂开一道巨大的缝隙。
张沉对墓碑说:“我终于能放你走了。”
砰、砰、砰!钢棍和石碑的巨响在这座荒芜的墓园里接二连三响起,张沉砸下第二棍、第三棍、第四棍,直到把这座墓碑彻底砸塌,又抬脚在这堆破石块上轻蔑地踢了几脚。
接着他转身走到和墓碑并排立起的木桩前,望着这排破败的木头桩子,这些木桩上鲜红的漆早已在十一年间掉落得差不多,露出里面大片大片本来的原木颜色,歪斜着站在本就算不上牢固的土地里。
张沉在空中再次扬起胳膊,砰地一声用尽全力砸向这排自己亲手打下的木桩。
砰、砰、砰!第二棍、第三棍、第四棍……
直到这排木桩彻底倒下。
轰!远处忽然传来一阵爆破声,紧接着是无止境的轰隆声,整个城市都要被震得地动山摇。
张沉拎着钢棍,和程声同时看向远处的声音来源。那座在云城屹立了半个多世纪的巨大烟囱在这阵巨大的轰隆声里慢慢歪斜,沾满黑烟的砖石块像暴风雨一样随着爆破凶猛地下落,最后回归地面。
天空上方忽然飘起小雨,张沉走到程声旁边,扔了钢棍,咣地一声倒在他身边。
两个人在爆破声中平躺着,一起望向飘着小雨的天空。
震耳欲聋的爆破终于停下,程声等周围彻底安静下来,在雨中慢慢爬起身,手扶着刚做完手术没多久的腰和腿,吃力地一点点爬到对面正对着张沉头顶的位置停下,缓缓俯下上半身,倒着看他的脸。
张沉也在看他,脸上积存着天上不断落下的水迹。
看够了,程声伸出一只手把他脸上的雨水拂去,让自己的上半身挡在他面前,为他挡雨。
张沉目视上方,只看得到程声的胸口,用手戳了戳他,问:“你干什么?”
程声没挪位置,很认真地说:“我在给你挡雨。”
想了想,他继续说:“这辈子哥哥保护你。”
第76章 End
二零一零年(陌生人阿智自述)
第一次认识张沉和程声的那一天有些特殊,距离他们认识我还有三年,我因为和男朋友分手这件事哭了整整一天。
他说我根本不会爱人,咄咄逼人地一条条列举我的恶行:记不住他的生日、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玩什么、从不会主动买礼物、不会撒娇、看他时眼里没有光。
我说:“我连我自己的生日都记不住,你怎么能指望我记住你的生日呢?”
他那么一个高大的男人气得呼哧呼哧大喘气,指着我的鼻子诅咒我:“你根本就不懂爱,这辈子都找不到爱!不对,你根本就没长一双发现爱的眼睛,这辈子连别人的爱情都看不到!”
然后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啪嗒啪嗒掉落下来。
奇怪,我明明没有那么喜欢他,为什么会哭?难道我承认他说得对?
我背着包在大马路上漫无目的地走,正巧走到一家正在装修的酒吧门前。这家酒吧我认识,据说老板很是阔气,前些年盘了一批知名、不知名的乐队来店里演出,好吃好喝供着,有时还分给他们些酒水抽成。可最近行情不大好,那些不算知名的乐队大多数销声匿迹,再也没人听过他们的消息。
走进这家还没装修结束的酒吧时,我还在思考那个问题:为什么我没长一双能看见爱的眼睛?
想着这个问题,我往楼上走,背后的书包带却忽然被一个陌生男人一把抓住。
“姑娘,我们还没开业。”
拉住我的那个人眉眼平和,身材微微发福,我上下打量他一来回,估摸着这个人应该是酒吧老板,马上低下头道歉:“对不起,我喝多了,现在不太清醒。”
大概是酒吧老板有先天优势,天生能对付酒鬼和神经病,他很轻易谅解了我的不礼貌行为,把我带到一片狼藉的吧台,扔给我一盒解酒药,又去后面倒了杯温水端过来。
喝过药之后我好了很多,趁着老板还没起赶我走的心思,大摇大摆在他店里来回晃荡。舞台侧门有一面花花绿绿的大墙,我好奇地凑近去看,发现这面墙壁上贴满了照片,每张照片下都有具体年份。
最中央挂着两张显眼的大照片,一上一下,同样的两男一女,相隔十年,每个人变化都很大。
我还没仔细看,那个发福的老板忽然从我身后冒出来,一只猪蹄似的手指向正中央两张照片中靠上的那一副,很得意地说:“这是我十八岁时候的样子,是不是还挺帅?”
我回头看看老板现在这幅发福模样,再看看照片里那个清瘦的男人,可惜地点头,然后指向两张照片里最中央的男人,问老板:“他是谁?你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吗?”
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老板忽然愣了一下,但他很快回过神来,指着照片里的男人说:“我的发小,叫程声。”
他刚说完,我的眼睛恰好注意到离这两张照片最近的一张合照,也是两男一女,中间穿白衬衣的瘦高男人尤为扎眼,身上挂一把电吉他,胳膊搭在另一个抱着贝斯的人身上,眼睛随意地望向镜头。
我看着他黑漆漆的眼睛,好像看到了某种不一样的情绪,这种情绪让我没法移开视线,着了魔一样一直盯着他的双眼。看着看着忽然有股熟悉感涌上来,我好像在哪里见过这样的眼神,可我确定我不认识这个男人。
喜欢本文可以上原创网支持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