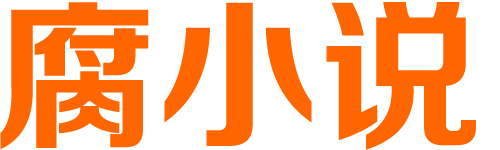偏执帝王的宠爱(48)
可别等他死翘翘了。
听说皇帝狗带的话,皇子要守孝好多年呢。
新帝要守孝吗?
顾宴生不知道,原著里好像也没说过的样子。
敖渊垂眸看着那张卷轴,唇角一挑,“我登基之日。”
顾宴生一愣。
敖渊复又说道:“这天下间,没有什么比帝后大婚更隆重的庆典了,我会给你最好的,到那时,你便是皇后。”
顾宴生张了张嘴。
他刚想说他不会,也不知道皇后平时要做什么。
然后话才刚要说出口,脑海里面便突然多出来了很多事情。
又像是突然想起来了一道久未做过的数学题一样,看到了问题,他就知道了解法。
然后他把话重新吞了回去,认认真真的点点头,捏着自己的小拳头,“我会努力的!”
*
又过了风平浪静的几个月,宫中不光传来了太子被软禁的消息,还传来了大皇子命不久矣的噩耗。
这下就连太医都瞒不住了。
敖渊在宫门口遇见了同样驾马赶去的敖武,两人并未多言,一同驾马走向了大皇子居住的寝殿。
两人到的时候,皇帝正双眸通红,坐在窗边握着大皇子的手垂泪。
而大皇子双眸紧闭,嘴唇泛紫,眼窝乌青,两鬓甚至也已经染上了白霜,俨然……大限将至的模样。
“朕问你们,瑞儿究竟如何?”皇帝的声音中气不足。
几个月来长久的亏空让他的身体也越发颓败,一句话而已,就已经比起几个月前来说大不相同。
御医长跪行几步,拱手道:“皇上息怒,只是大皇子……”
他咬咬牙,目光看见了旁边几个皇子滚着金边的靴子,紧闭眉眼说:“大皇子郁结于心已久,心结未消,早有五脏俱损之前兆……非药石可医啊!”
“一群废物!”皇帝果然怒不可遏,他站起身,重重踹在御医肩上,“他是朕的儿子,礼朝最尊贵的皇子!何来郁结于心一说!”
敖灵璧漠然的看了眼大皇子散发的模样,对这话恍若未闻,眼观鼻鼻观心,垂首坐在一个角落。
他也是除开大皇子之外第二个不需冲着皇帝行礼的皇子。
皇帝无能狂怒了一会儿,摔下一句“医不好提头来见朕”之后,便怒不可遏的离开了。
剩下的太医这才战战兢兢的起来,彼此对视,全都是满脸的愁苦。
屋内不多时被清空。
大皇子这才迟迟的睁开了双眼,似乎辨认了好一会儿,才认出眼前的都是谁。
他被人扶着站起来,手背、胳膊、乃至脖颈都全是被太医施针后留下的针孔。大皇子恍若未觉,撑着自己青紫又夹杂着斑驳血点的身子,虚虚抬起手,指着屋内的几个凳子,“都坐吧。”
敖灵璧看着大皇子,说道:“皇兄这是何意?”
“何意?”大皇子抚着胸口,看着敖渊说:“父皇不愿处置太子,一味偏袒维护……我日夜遭受焚心自问之苦,我是何意,你不知道吗?”
敖灵璧沉默不言。
他看着太子的模样,轻笑一声说:“我自然知晓。”
大皇子喘了几口气,看着敖灵璧的双眼,突然也笑了声,说道:“是,你也懂我。”
敖灵璧生母被皇帝逼死,说她受不住双生子的福气,将他们兄妹二人从生母身边夺走,给了别人养。
其后虽诸多宠爱,却又将自己最疼爱的小公主嫁给了年近七旬的羌王。
被问及为何不愿时,敖灵犀将这缘由说了,却更引来了皇帝怨怼。
因皇帝也年近七旬。
如此周折之下,唯一的妹妹也惨死他乡,骨肉无存。
而提出这奸计的人,不也正是太子吗?
敖瑞闭了闭眼,看着敖渊说道:“时机差不多也已经成熟了。我瞧着父皇那模样,已经……糊涂了。”
“肆意妄为,暴躁易怒,纵欲纵情,除了蓝贵妃,没人能贴的上他的边儿——当年太子用在你身上的药,大约他自己和父皇到死都不会知道,那药会被用在他们自己身上。”
敖渊沉默不言。
过会儿,他说道:“他最后会怎么死?”
这是极为大逆不道的一句话。
可敖瑞却像是在说今晚吃什么,“血液倒流、爆体而亡,尸身僵硬无法固定,然而……金枪不倒。”
敖渊脸色冷了冷。
大皇子一顿,说道:“你也已久未毒发,说不定是扛过去了。”
敖渊却没有回他。
只默默的说:“你接下来,待如何做?”
“在给父皇最后一剂猛药罢。”他似乎已经是倦了,身子不住的往下滑,“太子入冬以来,许是因为气温降低,他稍稍收敛了些。待到开春之日,我留在他身边那人,便会崔使着加大他的药量,让他没日没夜找他当日用来克你的美人儿饮鸩止渴……”
“最终步入死亡。”
*
敖渊带着滚滚寒气重新回了王府。
顾宴生这段时间好忙好忙好忙。
脚不着地的那种忙。
因为心知自己未来可能要肩负起多大的责任,他这段时间几乎是没日没夜的在学习——练字也好、熟读默背也罢,他甚至还去了很多次备考学子们经常会去的地点,蹭人家的课听。
为此,居然还因为对上了几次诗,又什么都敢往外说,而留下了个美名。
见着敖渊回来,顾宴生手也不停的把一根毛笔往头发上插——这是之前跟着路边一个卖发饰的婆婆学的。
那个婆婆就把头发那么一披散,随手再拿着一根簪子,就能把头发全都盘住,在脑袋上固定一个包包,怎么用力都不会散。
顾宴生在这里一段时间,绑头发绑的脑瓜子生疼,便磨了很久学会了。
可惜他脑袋上的头发好像有点多,在婆婆那买的簪子让他头发给掰断了。
刚断。
然后他就顺手插了根毛笔。
见敖渊回来,顾宴生双眼亮亮的就捧着自己的字走上去,喊道:“圆圆你看!师傅说我字迹进步很多——快要和从前差不多了,也终于有了些风骨了!”
毛笔字这东西,顾宴生总是脑子会了……但是手不会。
他甚至找出了很多以前的字画,照着临摹都不行。
明明知道那是自己的自己,找碳棒来也能写出差不多的,但是一换成毛笔,就成了软趴趴的一坨。
敖渊压了压自己的情绪,看了眼那张字,趁着嗓子应了一声,“嗯。”
顾宴生将纸缓缓放下了。
然后他看着敖渊,慢慢的说,“圆圆你不对哦……”
他上前皱着鼻子轻轻闻了闻,旋即又仔细观察了一下敖渊的脸色,说:“宫里出事了吗?”
敖渊抿着唇,缓缓点头说:“大哥时日无多。”
“啊。”顾宴生点了个头,想想说:“正常的。”
后半句被他吞了回去。
按照原著,大皇子会死。
而且大皇子是唯一一个不是敖渊动手才死掉的皇室……他正经是被自己给愁死的。
所以顾宴生就怕自己会伤心,一直没有很敢和大皇子多说什么话。
就连提建议,都是隔着敖渊的。
敖渊看他半晌,说:“今日闲聊说起了太子与父皇身上中的药。那药不可解,唯一的一个解药,现在就在太子身边,那叫顾怜儿的婢女身上的奇香。可那个香气,会令人上瘾,每次压制过后,下一次便会数倍爆发,最终……”
“最终活不过五年,而且死的特别惨,对吧?”顾宴生认真的说。
敖渊双眸沉沉,握紧了自己的拳头。
他闭着眼,沉声说道:“过些日子,我便向……”
向父皇请旨,取消了他们的婚约,不再耽误顾宴生婚娶。
可念头这么想着,敖渊的瞳色却愈发变红,以至于双眸都变得通红。
喜欢本文可以上原创网支持作者!